

电话铃响,叮呤呤呤叫起来没完没了。我用被子蒙住头,伸一只手出去 摸索话筒。
“哈喽?”我把话筒拖进被子里,闷着声音问道。
电话里传来一把女声,嘻嘻哈哈地笑着,背后有人在催她:“快点啦, 她到底去不去?”
我当然知道这是谁,拉开一角被子,看看钟才将将六点。我呻吟。
“你们要干嘛?”我沙哑着嗓子,几近于乞求的味道。“我才躺下。”
“小妹妹,出来玩啊。”又是一阵尖笑,我把话筒拿得远一点,“去滑 雪吧,我们三十分钟后上你家按铃。”那边电话被人抢了过去,一把男 声插进来说:“动作快点儿,别让我们等。”
电话挂了,剩下我在这头抓着话筒发呆。三十分钟,他们只给我三十分 钟。
“哎,”我推推枕边的人,“我要去滑雪了。”
“噢。”他说。
“今天不回来了耶。”
“哦。”他转个身,用被子盖住头。
我等等,看没啥子下文,就起来了收拾包袱。临出门的时候,我们家那 位倒醒过来了,看看我,问:“还在啊?”
“这就走了。”我拎着背包出了门。站在街口等车,我发现自己穿的是 拖鞋;可他们车子已经到了,拖鞋就拖鞋吧。
上车的当儿,我偶一抬头,看见了澄蓝的天。

一大早,路上没甚么车子,我们的面包车不徐不疾地开着,也很有点奔 驰的意思。
开车的先生同他后座司机的太太在耍花枪,男的板着脸,女的嘟着嘴。 后座里的一对小情人嘀嘀咕咕地说着情话,无非是今早起床的时候你怎 么那么慢然后等下滑雪的时候你要看住我点之类。坐我身边的两位仁兄 看来是初会,递完名片后,两个人一叠声地“以后请多指教”,听得我 大大地打了个哈欠。
看来我是落单了。我拉过大衣盖在身上,开始倒头大睡。车子里放着伊 伊呀呀的日本儿歌刚好起了催眠作用。
中徒停了一次,我下车买咖啡喝。启明君排在我前面,回过头上上下下 地打量了我一番,“大姐,我们是去滑雪,just in case you don't know。”
我低头看看我的鲜红色四寸高跟拖鞋,木着脸问他:“你有意见吗?”
“你看起来像快要死了。”这是他给我的评语。
废话。这还用他告诉我?我累得要命,连白眼都省下了。
等我的咖啡喝完,我们已经进了山里,车子在盘山路上爬着。雪早融了 大半,没融的也变得黑七麻乌,一搭搭脏兮兮地覆在树丛与树丛间的黄 土地上,像狗身上生的癞。
雅玲林宾一早和好,雅玲正咕咕笑着剥了桔子喂林宾吃。文文靠在家敏 的肩上盹着了,家敏则跟启明建华讨论着股市的最新走向。啧啧啧,硅 谷工程师协会里出的社会栋梁们呦。
我靠着窗,又闭上了眼睛。出路,我的出路也不怎么样嘛。

雅玲跟我都不滑雪,我累,她懒。
“我们去逛街吧。”我躺在旅社的沙发里问雅玲,整个人摊开呈一个“ 大”字。出都出来了,总该要出去逛逛的。
“好啊,好啊。”雅玲很起劲。一说逛街这女人总是高兴的,反正花的 是她老公的钱。“去Reno还是去Tahoe?”
“Tahoe吧。”我想一想,“Tahoe近点儿。哎你认得路吗?”
“不认得啊。你认得吗?”
“也不认得啊。”我抄起了钥匙,“走吧。”
兜了几个圈子,Tahoe市终归还是被我们找到了。雅玲很失望,“ 就这么一条街呀?”
“有这么条街已经很不错了,”我饿得前心贴后脊梁,“找东西吃吧。 饿都饿死了。”
我随便找了个车位停下,顺着正对着的巷子望下去,隐隐约约看得见一 汪子水,白花花的颜色。小巷子里挂着三两个吃食店的招牌。“就是这 儿了。”我拉起雅玲顺着巷子走下去,近四十五度的斜坡,雅玲在我身 后啧啧连声,“小心走好。”她说。
巷子的尽头是一栋木屋,两层高。上面一层挂着个中文招牌:京川。我 和雅玲一起摇头。跑这么大老远地来吃蹩脚中国菜?开甚么玩笑!
雅玲说,“走吧,先爬回上去再说。”
我说,“等等,先找找水吧,刚刚在上头明明见着来着。好不容易走下 来的。”
我们绕到木屋侧面,我发现了水,雅玲发现了一扇小门,我们俩一起欢 呼。雅玲马上说,“是pizza,我们先吃pizza。”
确切来说,我发现的是木头阳台下的黄色沙岸与躺在沙上的鹅卵石,水 声哗啦哗啦地响,却看不见什么。先吃东西。这一点上我同雅玲很有默 契,民以食为天嘛;至于湖,吃饱了再找也还来得及。
小门里面是条昏暗狭窄的通道,一只暗红色的灯泡自霉迹斑斑的天花板 上垂下来。我们怀疑这是间地下酒吧。通道末段又是一道木门,我们拉 开门走进去。我的眼前猛地一亮。
湖。湖哎!
明灰色的一片汪洋坦坦荡荡地呈现在我们面前,水面一望无际,终于在 视线尽处与空旷苍白的天空溶为一体。右前方极远处隐约屹立的该是雪 山,白雪皑皑,一时竟分不出哪里是山、哪里才是天空;唯有细细的一 线墨绿把山与水划分开来。
“哗--”我张大嘴巴感叹,“哗!”
不虚此行了。
小店里不过才摆了三五张桌子,却围起了个喏大的吧台,对着湖的一面 墙打通,嵌着整块的玻璃。店里没什么人,我们的pizza却隔很久 才送了上来,我和雅玲坐在靠窗的位子上慢慢嘬着冰茶晒太阳。窗外挂 着的风铃叮当作响,我伸手出去拨弄细竹的帘子,不禁摇头微笑。这家 店的主人真该是个风流人物。
雅玲絮絮叨叨地同我谈心,我托着腮听她诉说着关于人生的大道理。我 很享受,时不时地“唔”一声鼓励她说下去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几乎任 何事都会是愉快的,我的眼神漫无目的地落在水面上。
服务生送过来两杯啤酒,笑说:“on the house。”
雅玲很诧异,抬起头问:“为什么?”服务生是个有着金棕色皮肤褐色 头发与眼睛的大男孩,他只是笑笑,告诉雅玲:“just because。”
我已经开始喝,一口气灌下去一大半。雅玲还要追问,我按住她的手, “嘘--”我指着从水面上掠过的水鸟告诉雅玲,“嘘。看,你看。”
雅玲不响了。我喝干了啤酒,对着若隐若现的闪闪鳞光眯起了眼睛。这 是我的假期,我的假期已经开始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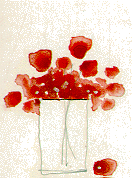
风陵渡并不是它的真名,天黑了的时候我们一群人在那里吃晚饭,蒙古 烤肉。
那是一间弥漫着油烟气的小馆子,粘搭搭的桌椅,半褪了花色的塑胶碗 碟,墙上挂着封尘的大红宫灯,台子上的玻璃面下还压着英文版的十二 生肖图。柜台后面自助餐一道排开,靠墙打横了围出来的是烤肉用的圆 形铁板。
我们在滋滋喇喇的人间烟火声中灌着啤酒,一边目中无人地用中文交谈 着,声音随着体内酒精成分的增加而越变越大,其中还掺插着大动作的 肢体语言。
外面是彻骨地冷。偶而店门一开,寒风马上嗖地钻了进来,冻得人一缩 脖子;却又立马站了起来,指着空了的啤酒瓶子跟店家吆喝着:“哎, 再来半打。”
我吃得很多,以一种悲伧的情绪把一碟碟粗糙的食物塞进胃里。若有一 天,我们的文明无论是升华还是浮华,都将成为过去,一切留得住留不 住的人与事都变得模糊遥远;到那时,唯一靠得住的也不过是眼前的食 物与颈子里的这口气。
为了活命而吃,为了活命而活命。
我以为在山上的夜里,人的心会比较静,比较能够接触到文明以外的本 性。天知道,也许我们在座男士们的本性就是标准的栋梁之材,话题从 电脑软件一路扯到股市上落,就此停滞不前。我捧着头,瞪着天花板。 想是为着我穷的缘故,等我也炒得起股票了,很可能比他们还要投入。
侍应生又拿出半打啤酒,这回却说:“老板请客。”别说是雅玲,连我 也开始讶异。顺着女侍应生手指的方向看过去,我们看见一张脸,似曾 相识。雅玲同我齐齐笑了。
“为什么?”这回是我问。
“老板说难得有缘,一天里碰见两次。”那女孩子这么说。
也不由得我们不信,那位文质彬彬、带着浓厚书卷气的餐馆老板到我们 临走也没过来打个招呼。看来他的款待,真的只是为了有缘。
呵,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。
【夜话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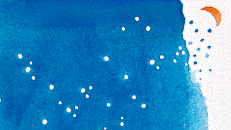
“日子过得怎么样?”启明问我。他坐在滑雪场门口的长椅上,跟我借 火点起一支烟。我正仰着头满天地找那颗慧星,见他问,顺口答道:“ 不怎么样。Man, life sucks。”
“Alright!”启明伸出一只手,“give me five。”
我骇笑,转过头来,与他一击掌。
“怎么?出来散心啊?”他笑问,“你又不滑雪。”
我笑笑,不予置评,把大衣的领子拉得紧点。好在没风,不过也足够冻 得我们俩直打哆嗦了。
隔了一会,我问启明:“你呢?日子过得如何?还找不着女朋友?”分 开了再久的老朋友也还是老朋友,有话可以直说,不怕误会没有尴尬。
谁知道启明君忽然忸捏起来,一双腿伸直又收回来又再伸直。我侧头看 看他:“干嘛?我说错啦?”
他想一想,嘴巴张开又合上。我深深纳罕:这人怎么啦?跟我还有什么 说不出口的?
终于,他决定说话:“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告诉别人。”
我一听就乐了。“哟,秘密啊?”我闲闲地笑,“要真是秘密就还是别 说了。我这人嘴巴出名的大,保不准喝多了两杯就把你捅了出去。”
可他这话不说出来实在难受,他侧起头想想,还是打算一吐为快:“好 吧,好吧。不是秘密,反正你也不认识那个人。”
我抿着嘴偷偷地笑,听他诉说他的故事。
“我在学校里一直都没找过女朋友,这你是知道的。”启明从我手里接 过啤酒瓶子,仰起头灌了一大口。他的眼神开始迷离,声音变得温柔。
说开了,启明的故事十分普通。
他在学校里办活动的时候认识了这个女孩,她那时候才大一。好家庭出 身的小孩子通常单纯,这女孩子被家人照顾,十八九岁了还天真得不像 话,整个人是一张未曾落墨的宣纸,轻、软、纯洁。他打自一见面就开 始喜欢她,但终归还是舍不得落笔。没料到一个学期不到,他的宣纸就 被人给打上了底色;学期还没完,他的宣纸又被人团一团给丢了。启明 君义不容辞地忍着心痛负起了安慰开导她的责任。可受了创的心灵哪是 那么容易平复的呢?她又为了选修学科的问题同家里闹得誓不两立,另 加上些别的麻烦,几桩事加在一起,女孩子一气之下头也不回地走上了 浪荡之路。
男朋友走了,学被退了,又不容于家里,女孩子晚晚哀哀痛哭,哭完了 却又上起浓妆出外冶游。凌晨,喝得烂醉,回来再接着哭。日复一日, 所有亲友都离她而去,除了启明。女孩子心存感激,一叠声地赶着启明 叫大哥,启明心里虽是一万个不原意,却也只有受着。
“这时候要告诉她我不想当她大哥,倒好像我趁人之危似的。”
我摇头。要真是喜欢她,这危,趁了也就趁了;这么骄傲这么君子做给 谁看呢?不过我的道德标准一向卑微,我承认自己是个没有水准的人。
启明接着说下去。
后来,这女孩子单身跑了下去LA,(怎么大家都爱往LA跑),启明 毕业了,也冲着罗省找到了份工作,跟了下去。也不求什么,不过是想 跟这女孩子近一点,多个照应。
终于,有一天女孩子的酒醒了,决定回去念完她的文凭。启明虽然不舍 得,但为了她着想,也还是鼓励她搬回家,一路把她送了回去,交到了 她父母手里。
“那多好,”我忍不住插嘴,“你们大局已定了嘛。她又回来走上了黄 砖路,你们的前途简直是一片光明。”
“我们已经两个月没通过音讯了。”启明是说不出的沮丧。
我张大了嘴,“为什么?”
“每次我一对她好一点,有点那个意思,她就打退堂鼓了。最长的一次, 她失踪了整整八个月。”
“你把人家怎么了?”我瞠目结舌,“她怎么吓成这样?”
“怎么也没怎么,”启明很懊恼,“不过是告诉她我很喜欢她嘛。看来 她现在还没准备好。”
“啊--”我明白了。
我知道我很扫兴,但还是忍不住问他:“你有没有想过,人家只是把你 当大哥,不打算跟你怎么样?”
“不是的,”启明很固执,“她只是现在还没准备好。”他又来不及地 跟我解释:“她才刚刚结束了一段很不愉快的关系,暂时只想好好念书, 赶快毕业。”
“哈!”我不说话了。他要是愿意这样相信,又能从等的过程中得到快 乐,就由他去吧。我是谁呢?这位堂堂的工程硕士又不是白痴,何用我 来做他的指路明灯?
唉。
“哎,”故事听完了,我站了起来,“回去吧。冷呢。”

大家一致通过,早晨叫我起床是最艰难的一件差使。
我只是不明白,我们明明是十点钟才要出门,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在九点 四十五分之前把我挖起来。
建华一连声地骂我,“以后再也不带你出来了。”他说。
我一拧头,“谁稀罕。”
回去的途中,建华是下定了决心要跟我过不去,一路上他都在挑我的毛 病。
“你哪里弄来的这双鞋?红色拖鞋很庸俗你知不知道?”
“衣服要么穿好要么脱下来,不要吊儿啷当地挂在身上行不行?”
“哎哎哎,头发不要乱甩,你当你是沿街叫卖哪?”
“你为什么走到哪里都要抱着个背包?没有人会偷你的东西。”
“笑得那么大声干嘛?生怕人不知道你是八婆是不是?”
“咦你怎么不说话了?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器?”
……
气得我。终于我忍无可忍,对着他暴喝一声:“陈建华,你闭嘴!”
他倒咧开嘴笑了:“哗,狮子吼。”

道一声别离,忍不住轻轻地抱一抱你。
最终还是到了说再见的时候,我与每个人拥抱话别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 能再聚到一起。一转头,我的眼眶红了。好在有风,只需推说是沙子飞 进了眼睛。
回到家,我意外地发现台子上的花换过了,餐桌上还摆着一支红酒。我 心里一动,可是有人要给我一个惊喜?
在公寓里转了一圈,没有人,却在桌子上找到了一张字条。上面说:
我微微笑,吁出一口气。真好,一切如常。看看钟,我应该还有足够的 时间洗澡洗菜,然后在他们回家之前赶出去。
一切如常。我打电话给妮妮,“喂,出来吃晚饭吧。”